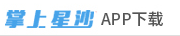云南游记
◎胡锐祥
飞机起飞了,此时腾冲的早晨兼上午是大雾天气,能见度极其糟糕。但行程本就由六点调到了九点,到现在十二点多才登机,不能一拖再拖了。飞机几乎在一瞬间完成加速,我陷进座椅里,之后窗外变得恍惚,一切都被白色照得无处遁形。
如果要我给时空隧道一个假想的话,这就是了。
我能感觉到自己离地面越来越远,但我听不见,更看不到。此时的我只能有两个选择:一,盯着回忆发呆;二,做梦。我认为现在我是两者皆有之,毕竟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。
从近的想起,在我脚下的腾冲。你当然可以说它是一个鸟不拉屎的穷疙瘩,知其名的甚是不多,但我们更愿意认为它是一片热土。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发起地,没有鲜血溅到一株小草上、一块沙砾上、溅到小溪里、浸到泥土里,这是不可能的。比起让人流连忘返的大小空山和湿地,我印象最深的果然还是国殇墓园。“未成年而死为殇”,为国而殇,是为常人之不可及也。所谓替你负重前行的人,无非都能影射到这些人。由于政治原因不得揭开雾霭而重见天日,或许那才是真正的悲剧。
蒙自,相似的先入为主的观念,或更甚于腾冲的农村印象,立足于滇越铁路和“碧色寨”的雅称,得以发展经济,实现小康。它让我感到的可能是一种国耻,原因不过是法国的租界在此罢了。我在两篇关于蒙自的散文里多次提及,然后自己给自己解嘲,说要谅解过去但不能遗忘历史,诚惶顿有。实际上,我似乎又一直在为法国人开脱,正是他们帮助改善了当地的状况。时至今日,这已经成为了蒙自的一个重要元素,不管是人文特色的还是历史方面的。
昆明,省会城市。初次见到的即是滇池。这里水高云低,带来的不是压迫感,而是一种宏远的意境。满腹才思的人当然可以赋诗一首以抒怀,而我独倚栏杆,听风的声音,这也无不为一大乐趣。
谈到昆明我不得不说两事,一是西南联大,二是闻一多。前者和后者从属关系,但既然是在昆明,那还是把闻一多挑出来仔细讲为好。硬汉、英雄,这些词在什么时候能和身子单薄的书生扯上关系,可能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那八年最具代表性。西南联大的精神大家都懂,西南联大的衣钵还需有人传承。而其中必然有一个闻一多,我们有一个小组专门谈及了他的早期作品。大意是他的早期作品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,从而表现得爱国主义情怀明显。需要注意的是,在今天,这一课题也绝对有意义。他在昆明有故居,很安静,并没有大张旗鼓当作旅游胜地。与他的性格真是不相符。但也许这就是他追求的。
不知不觉飞机已飞到比云还高的地方了。太阳很大,但感觉并没有在云雾里亮堂。不过也算是豁然开朗了。
在云中和在云巅之上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如果说前者是回顾,那么后者便是总结。
从来云南的第一天,我就没觉得这是“夏日青春漾”。这里最高温也不上二十度,气候凉爽舒适,偶尔看见一两回太阳,更多的是云和雨。但这里确实有青春,不管是我们自己的,亦或是西南联大师生的、中国远征军的。我们用文字把他们记录下来,想象每一个最真实最感人的情境,这也就是一种成长了。
关于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文学社成员,尤其是自己组的,虽性格各异,有的不善言辞又文文静静,有的热情开朗且乐于助人,有的才思敏捷而精明能干,有的外表高冷却内心柔软。但他们组成的共同标签,叫文学,叫人文关怀。就像眼下的云海,连成一体,方能风起云涌,让人感其宏远,慨其辽阔。这便是我们的内心世界,精神世界,你可以在其中穿梭,亦可以携其水雾,把它带到无尽的远方。
然后,伴随一声巨响,飞机着陆了。它渐渐地减速,慢慢把我拖回现实世界。我终于发现,梦本来就是如此,短暂,美好,又有无声的教育意义。但愿,我把双脚离地的每一刻都能定格。
再见了,云之南——云南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