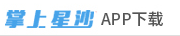我的梦,我的河
◎唐池子
我记不得那些梦与醒之间的梦是几岁开始,六岁、还是八岁,我说不清,它不完全是梦,因为感觉醒着,什么都能看见;但它又不完全醒着,意识留在梦的边缘,混沌、迷糊、朦胧——
我听见越过竹林的一阵风,吹过青黑的瓦顶,呼,呼,呼,朝我而来。那风是绿色的,是深翠绿,像我家后塘里那只翠鸟羽毛的颜色。我看见自己小小的身体,像艘小小的船,在这阵风里摇了摇,马上飘了起来,越过了我家的老宅子,越过了竹林和好多山茶花,越过了调色盘一样花湾的田野。我看见了两条带子一样的河堤,圈着银子一样的河水,接着嗅到了一股子青草和大河混杂的强烈气息,这种气息非常有力,让我的身体瞬间似乎有了质量,我看见自己正在微笑着缓缓降落,降落,落在我们的银雪河上。
我心里仍然是没有惊讶,心知肚明的梦。这条灌溉滋养我们的河流,在我眼里,它也是一只眼睛呢。在我童年世界里,我觉得银雪河就是世界的一只眼睛,是世界明眸善睐的一只眼睛,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一只眼睛。它延延绵绵,汤汤的河水,不知道从哪里而来,又流动哪里去。也许大人会告诉你,它来自哪里,又去到哪里,可是真正的部分,你没有亲自陪它一起流过,谁知道呢?它有那么古老的传说,那么,它一定流了几百年的几百年了,它不老吗?它从春流到冬,不累吗?它晒了那么多太阳,不黑吗?它不老不累不黑,总是奔流不息、满川银白。它真的是一只非常神奇的眼睛,我盯着它,一个劲儿盯着它看,想把它看穿,我看见了它的眼球,绚烂缤纷的眼球,那一刻,我像窥见了整个浩渺的宇宙。这条河,对我不是从此岸到彼岸,是浩浩荡荡地向未知的前方奔涌而去,是梦的路,是想象的床。花湾,是我的第一个渡口。银雪河,是我永远的航道吧。
我记忆中有俊美的外公,记得很深,记得他住在银雪河的一头,记得他的蝉眉,记得他的肩膀,但我不记得他唱过戏……我的父母都会唱花鼓戏,花湾人人都会哼几句,我的父亲很会吹笛子,我隔壁的老叔会拉大筒,我的确有一个会唱戏又貌美的兰姨,多病的舅舅,身材迷你的外婆……有一天,我听妈妈叹气说了一句:“可惜我这辈子没演过小姐,年纪太小了,你外公办过一个戏班子。”这句话,在我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叹号,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很多年过去了,没想到当年妈妈一句叹息,让我真的产生好奇,动笔写了外公的戏班子。一切都带着记忆中那种梦与醒之间的飞翔感,我一定会从银雪河出发,向记忆的上游回溯,那个上游就是我混混沌沌的幼年生活的象征。我说过,我要找回去。
我无法不敬爱我的外公,我在自己创作出版的《满川银雪》里表达了从童年时代以来对他的崇拜,那是一个孩子对点燃过她心灵的亲情世界的全心向往。孩子总是什么都想懂,偏偏什么又不懂,除了爱——谁真心爱他们对他们好,谁也不用教,他们天生就懂。
为了幼年一个模糊的影子,为了存了那么多年仍然完好无损的珍贵的爱,我勇敢地去寻找外公的世界,尽管他已经消失多年。我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当一个花鼓戏迷,我先认真看了一遍童年耳熟能详的名剧,我惊讶地发现,这些故事、人物居然如此精彩,仿佛童年得到他的好,只是一次模糊的复印,这次才现了真身。
真的像游进了历史的银雪河,我开始查找长沙花鼓戏、浏阳花鼓戏的历史,又对照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的中国农村发展现状,然后细看这段时间花鼓戏的曲目,大概2、30部,花鼓戏全部用方言唱的,这几乎是我离开家乡以来听乡音最多的一段时间,真不矫情,我从来没有觉得家乡的方言如此动听,对湖南人霸蛮的精神和火辣的性格、尤其是湖南辣妹子的形象有了更深的认识,花鼓戏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这些鲜明的特点。
在做好这些工作准备后,我才构想故事结构,我几乎是顺着银雪河哗啦啦的水势来写的,一切如卷眼前,因为银雪河懂人的心,也懂大筒的乐声。
外公最后安息在银雪河边。银雪河边的花鼓音,会像银雪河的水流声一样,永不会消失。也希望,我拥有更多阳光流淌的早晨,被阁楼上的纺车唤醒,让我那个梦与醒之间的梦,在我的河上轻盈飞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