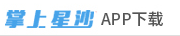腊肉飘香年味浓
◎王元辉
“细伢子盼过年,大人盼插田。”小时候我最盼望的,就是过年,盼着噼啪作响的“擦炮”,盼着过年的新衣,更盼着吃上晶莹剔透、香气四溢的腊肉。那“惊天动地”的咸香,让我能干两大碗饭,恨不得把舌头都吞下。
冬至过后,风越发冷冽起来,气温下降了,正是做腊肉的好时节。这时候回老家,家家户户的阳台上,院子里,或用铁钩或用竹竿挂起的猪肉,一条条在阳光下泛着油渍,特别壮观。这些猪肉在寒风里招摇着,慢慢变色、紧实,最后用米糠熏制,色泽红亮、香气扑鼻的腊肉就做成了。
听奶奶讲,做腊肉最好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,太肥会腻口,太瘦会很柴,都不好吃。她选的总是最漂亮的“七层楼”肉。所谓“七层楼”,就是一层肥肉,一层瘦肉,这样层层叠加的肉做出来既不油腻,又有嚼劲,为腊肉中的上品。
奶奶把肉买回来,先用烧红的火钳把猪皮烫得焦黑,然后用刀刮去上面的脏东西,加了盐揉搓均匀,一块一块放进瓦缸里腌起来。“鱼三肉七,腌一个星期就好了。”奶奶笃定地盖上盖子,防止小猫捣乱,只每天去翻拌两次。在年少的我看来,奶奶就是做菜的高手,她腌肉只放盐,做出来的腊肉却是最好吃的。
肉腌好后,奶奶把肉拿出来好好清洗干净,再烧一锅水,把猪肉一条条在滚水里过一下,这样蔫头耷脑的肉条就很有型了。奶奶拿着早就准备好的棕树叶把肉串起来,挂在竹竿上晾晒。奶奶在暖阳下纳鞋底、缝衣服,风吹起她的白发,也吹过惨白的猪肉,留下岁月的痕迹。我也搬一张椅子坐在一旁,看看奶奶忙活,等肉吹干。
猪肉在风吹日晒中渐渐把柔软收藏起来,有了硬硬的外壳,颜色也渐渐变深,有了小麦肤色,有了硬汉的样子。这时,奶奶会把猪肉取下来,一块块摆在铁筛子上,把筛子安置在大灶上,灶里生了火,撒上米糠慢慢熏,让那袅袅烟雾慢慢渗进肉里。奶奶说:“好东西急不得,一定要小火慢熏,香味才能进去。如果火大了,肉烤烂了,就不好吃了。”
慢熏出来的腊肉呈橙红色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柔软而有韧劲。一刀切下去,肉质晶莹透亮,在光线的映照下闪烁着微光,仿佛把一冬的时光都沉淀在其中了。肉熏好了,年就近了,年味就浓了。在那个物资不那么丰富的年代,奶奶的那盘炒腊肉,永远是新春餐桌上最稳稳的C位,最后一点汤底,也会被小妹拿去拌饭。那汪着油脂的饭粒都有浓浓的腊肉香。
肉搭百菜。腊肉可以和各种食材炒着吃,也可以和腊鱼一起蒸着吃,我最喜欢用风吹萝卜干炒腊肉。因为经过风的调教,萝卜也变得不一样了,少了青涩,多了些厚重,和烟熏火燎过的腊肉成了绝配。鲜萝卜配鲜肉是青春的爱情,热烈而张扬;吹萝卜干配老腊肉,则是知己间的懂得,那种醉心的归属感,配上越来越近的年味,即便身在天涯,也觉得心和家乡和家人在一起,没有背井离乡,没有孤苦伶仃,只有温情如初。
儿时腊肉的香味一直在味蕾深处萦绕,勾着胃、馋着心。如今,我也会在冬天买些五花肉回来,照着奶奶做腊肉的步骤,挂在阳台的护窗上吹干,再在淘宝下单买了米糠,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,找个空地用纸箱围起来慢慢熏成腊肉。于是我家每年的年夜饭上,都有一碟可以慰乡愁、可以代表年味的腊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