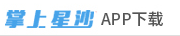追星星的人
◎吴丹
7年前,新学期的前一天,我收到一封来自星星的信。
开学前的教师会议刚散,我捏着那封信,在空教室里坐了很久。

信纸是浅黄色的,字迹工整得像是印刷体,却又在笔画转折处泄露出细微的颤抖。这是一位母亲写来的,关于她的儿子——即将成为我班上学生的男孩。
“老师,我的孩子来自星星上。他不是不听话,只是活在自己的宇宙里。如果您愿意慢下来,等等他,或许能看见他那个世界的光。”
我把信折好,放进抽屉最上层。明天就要开学了,我是刚刚到新学校接手一年级,学校特意把“特殊”的孩子放在我的班上,这既是信任也是重担。
漫长的等待与微光
九月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教室,我在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。大多数学生已经有了小学生样,唯独他躲在母亲身后,手指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。
“叫老师好。”母亲轻声引导。
男孩抬起头,那双眼睛清澈得像山涧的溪水,却仿佛蒙着一层薄雾。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,又低下头去,嘴唇动了动,没发出声音。
“没关系,小太阳,我们慢慢来。”我蹲下来,与他平视。这是他妈妈在信中写的乳名——小太阳,多美好的期待。
母亲眼眶微红,感激地看我一眼,轻轻推了推孩子的后背:“放学妈妈来接你。”
开学典礼的哨声成了这场“追逐战”的起始枪。
队伍刚排列整齐,一道身影突然窜出,向着与集合地点完全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。我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——那是小太阳。
“小太阳!”我喊着追上去,高跟鞋在操场上踩出慌乱的节奏。
孩子在前面跑,我在后面追,新生队伍爆发出阵阵笑声。校长正在台上调试话筒,看见这一幕微微皱眉。我终于在篮球架下抓住了小太阳的手腕,他用力挣扎,发出不安的呜咽。
“不怕、不怕……”我喘着气,尽量让声音柔和,“只是去听校长讲话,很快就结束。”
他安静下来,疑惑地看着我,似乎在我的表情中寻找着什么。我拉着他的手走回队伍,孩子们窃窃私语,几个调皮的男生做着鬼脸。
这仅仅是开始。
上课铃响后的第一件事,不再是打开教案,而是满校园寻找小太阳。厕所、图书馆、操场角落、甚至食堂厨房,他都可能突然出现。学校教师大群里,时不时就会有老师拍到他随地大小便的照片@我:“吴老师,来看看是你们班的孩子吗?”
每次我都红着脸去“认领”。小太阳通常安静地站在原地,眼神游离,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。

教室里更是战场。数学课上到一半,他会突然拍桌而起,绕着教室奔跑,大声唱着不知名的歌。美术课上,他把美术材料糊在课桌上。体育老师的投诉最频繁,因为小太阳拒绝听从他任何指令。
家长们的电话接连不断:
“吴老师,我家孩子回家说没法专心上课,那个特殊孩子老是吵闹。”
“我孩子学他拍桌子,这还了得?”
“刚进一年级就坐不住,能不能给他换个环境?”
教师会议上,也有人委婉提议:“是不是该考虑特殊学校?毕竟咱们资源有限,班上还有四十多个孩子要学习呢。”
我站在教导主任办公室门口,手里攥着那封浅黄色的信,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进去。那天放学,我约小太阳的妈妈见面。
咖啡馆里,这位母亲始终没有碰眼前的咖啡。她的手指交织在一起,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
“吴老师,我知道给您添了很多麻烦……”她声音哽咽,“小太阳本来就比班上孩子年龄大一些,如果他还不到正常孩子生活的环境中去适应,那他以后怎么适应社会……”
她打开手机相册,给我看以前的照片:小太阳在舞台上朗诵诗歌,小太阳在演唱比赛中得奖,小太阳搭积木、弹钢琴……照片里的孩子眼神明亮,笑得灿烂。
“他不是不懂,只是需要更多时间。”母亲说,眼泪终于落下来,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。
那天晚上,我查阅了大量的特殊教育文献,一页页地重新阅读。第二天,我开始了新的尝试。
我在教室角落设置了“小太阳的星空”,当他感到不安时可以进去待一会儿。每个课间,妈妈带他去厕所,建立固定的如厕时间。上课前,我会抓着他的手,轻轻告诉他一节课的大致流程。课堂上妈妈作为影子老师,也一直在努力。
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。他仍然偶尔失控,仍然有老师@我去“认领”,家长们的质疑也未曾停止。但我开始在群里发一些小进步的照片:
“今天小太阳安静地画了一整节课的画。”
“小太阳记住了全班同学的名字!”
“音乐课上,小太阳快速地学会了一首新歌曲!”
慢慢地,群里的回应变了:“真棒!”“继续加油!”“替小太阳开心!”
我召开了一次特别的班队课,让孩子们每人画一幅画,描绘他们心中的同学。出乎意料,小太阳出现在许多画作中——蹲在操场看蚂蚁的,专注画画的,甚至有一个孩子画的是自己和小太阳手拉手的画面。
“他上次扶我了,”小女孩认真地说,“虽然没说话,但他帮我拍掉了裤子上的灰。”
小太阳妈妈看着这些画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星光璀璨时
转变是悄然发生的。
某天早晨,上课铃响起,我习惯性地要去找人,却看见小太阳安静地站在走廊上,等着铃声结束再进教室——这是我们练习多次的规则:铃声太吵,可以捂住耳朵,但不能跑开。
我开始尝试带他阅读。最初的过程异常艰难,他连三分钟都坐不住,会把书扔到地上,甚至撕碎书页。我不气馁,每天坚持陪他读十分钟绘本,选择那些有明亮色彩和简单韵律的童书。
有一次,我找到一本关于星空的天文绘本,指着书中的星星对他说:“看,这是小太阳的星星。”他忽然安静下来,手指轻轻触摸书页上的星星图案,那一刻,我看到了突破口。
渐渐地,他从能坐五分钟到十分钟,从触摸图画到真正注视文字。二年级时,他已经能够安静地听我读完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到了三年级,每当我开始朗读时,他会主动搬来小椅子坐在我身边,眼睛随着我的手指在书页上移动。
而最让我惊喜的是,阅读已经成为他自我调节的方式。每当感到焦虑不安时,他会自己走到教室图书角,拿起一本书安静阅读。有时是天文图册,有时是童话故事,那些曾经被他撕碎的书页,现在成了他安宁的港湾。
深秋的一天,语文课上,我正讲解《秋天的怀念》,文中提到母亲病重却依然牵挂儿女。突然,教室后排传来清晰而稚嫩的声音:
“妈妈……也会疼吗?”
全班寂静。小太阳站在那儿,眼神不再是涣散的,他望着我,似乎在等待一个答案。
我走过去,轻声问:“小太阳是问妈妈会不会生病疼吗?”
他点点头,少见地保持了目光接触。
“妈妈们都会变老,可能会生病会疼,所以我们要学会照顾妈妈,对不对?”
他若有所思地坐下了,那节课再没吵闹过。
奇迹发生在四年级那年的春天。
音乐老师偶然发现,当小太阳听到钢琴声时,会安静下来,甚至跟着旋律轻轻摇摆。更令人惊讶的是,他能够准确重复听到的旋律,音准好得惊人。
“吴老师,这孩子有绝对音感!”音乐老师兴奋地告诉我。
我们尝试着让他参加学校的“三独”比赛选拔。独唱环节,他唱了一首《如愿》,声音纯净得像山泉,眼神专注地望着远方,仿佛真的在对着星空歌唱。
县级比赛那天,我比他还要紧张。台下坐着评委,评委们严肃地打分。轮到小太阳上台时,他紧紧攥着话筒,目光有些慌乱。我站在舞台侧面,对他比了个“大拇指”的手势——这是我们约定的鼓励方式。

音乐响起,他深吸一口气,开口唱出第一个音符。那一刻,整个会场安静下来。他的声音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,干净、明亮,像是星光照进现实。
他获得了二等奖。
颁奖时,他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,但当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时,他嘴角微微上扬,露出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微笑。
五年级时,他再次站上市级“三独”比赛的舞台。这一年,他选择了一首《有我》。比赛后阳光洒在他身上,他真的在闪闪发光,他不再需要我在侧面做手势,能够独自面对观众,完整地演唱整首歌。
他获得了一等奖。
学校的艺术节、元旦汇演、毕业晚会……小太阳一次次登上舞台。有时独唱,有时和班级同学一起表演。同学们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,甚至会主动在表演前帮他整理衣领,提醒他上下台的方向。
最震撼的改变在六年级上学期。一天早晨,小太阳妈妈激动地打电话给我:“老师,他说想自己坐公交车上学!”
我们制定了详细计划:我提前在车站等他,悄悄跟在公交车后,确认他安全到达。连续一周后,小太阳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这段路程。
毕业典礼那天,小太阳作为学生代表之一演唱歌曲。台下坐着看着他的我,眼角闪着泪光,满是欣慰。
典礼结束后,孩子们互相在纪念册上签名。小太阳安静地坐在角落,我正想过去帮忙,却看见几个同学主动走过来,把纪念册递给他。
“小太阳,给我画个星星吧,”一个女孩说,“你画的星星最好看了。”
他接过纪念册,认真地在扉页上画下一颗五角星,然后在旁边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——这是他练习了无数遍才会写的三个字。
学生们陆续被家长接走,教室空了下来。我整理着讲台上的杂物,忽然感觉有人拉我的衣角。
“要……要签名吗?”我问。
他摇摇头,把纪念册翻到最后一页,那里已经写着一行字:
“给追星星的吴老师:谢谢您等我发光。您的小太阳”
字迹工整,与他母亲那封信一模一样,显然是母亲代笔的。但紧接着,他伸出手指,指向那句话后的空白处,自己拿起笔,歪歪扭扭地添加了三个字:
“我 爱 您”
夕阳从窗口洒进来,给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。那一刻,他真的成了小太阳,发出的光足够照亮整整六年的所有艰难。
我蹲下来抱住他,感觉到他僵硬的身体慢慢放松,甚至有一只小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背,如同我曾经无数次安抚他那样。
照亮我的星光
星空从来不语,却藏着整个宇宙的奥秘。而有些孩子,注定要我们跑起来,才能追上他们的步伐,看见他们身上那颗星星的光芒。
教育是什么?不就是一场追逐星星的旅程吗?有的星星近在咫尺,有的却远在光年之外,你要拼尽全力,才能赶上一点他们发出的光,而那点光,足以照亮整个教育生涯。
我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,这是我和小太阳的故事。星空万里,总有一颗星星为你而亮。
(作者系长郡双语星沙学校教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