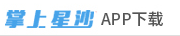五十岁,与秋同行
◎罗海亮
入秋,天干物燥。一条老狗软绵地趴在草丛里,扯长的脖子摊在地面上,一截粉嫩的舌头从微张的嘴里倾泻而出,时不时喘上一口粗气,来往的脚步声撑不开它那双热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。树上的知了有一阵没一阵地闹腾着。
一位嬷嬷牵着一个小女孩迎面而来。小女孩五六岁的模样,穿着粉色的裙子,扎着马尾辫,黑溜溜的大眼睛嵌在肉嘟嘟的脸上,蹦蹦跳跳的脚步,像一只蝴蝶在起舞。“老伯伯好。”稚嫩的声音从小女孩嘴里传来。我心底犯着嘀咕,现在的我很老了吗?我蹲下身子,拉着小女孩的手,微笑地哄着,“我不是老伯伯,来,再喊一次。”“爷爷好。”小女孩胆怯地喊着,明显感觉我的震惊,她的眼睛里也充满了疑惑。
微风拂过,路旁的松树纹丝不动,枯萎的松针无声地飘落,似乎在缝补这被童真撕裂的空气。我松开她的小手,拾起一根枯萎的松针,在手心里细捻起来。
抬头望去,慵懒的云朵或近或远的浮在天空,阳光随微风在蒸笼般的大地上晃荡,格外地刺眼。远处的山峦与天际接轨,那是天上与人间的分界线,上方是天空的深蓝,下面是稻穗的金黄。一茎开始微黄的斜草稳稳地、细细地在墙角里颤着。搭在墙头的葡萄架被浓密的葡萄叶遮盖,藤条不知什么时候探过了墙头。架下成荫,葡萄一串高过一串,有的掩映叶间,有的吊于高处,紫的晶莹剔透,绿的饱含青涩。我想,那是它们与秋同行时的颜色。而五十岁的我,在这个秋天里行走,已被酿成什么样的颜色呢?
我揣着慌乱的心情回家,站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起自己来。好像很多年以来,我都没有这么正式地端详过自己,仔细打量镜中的我,曾经对鬓角偶尔跳出来的几根白发嗤之以鼻,用各种染色剂简单梳理一下,轻轻松松地就阻挡了它的脚步。一直以为,我以黝黑的头发,标准的身材和较时尚的打扮,彰显着年轻。可鬓角的白发不断向头顶进军,它们醒目地倔强地生长着,毫无顾忌地展示着,向世人宣布它的存在。眉间不经意间多了一道川字纹,沟壑里掩埋着岁月的痕迹,眼角的鱼尾纹在似笑非笑间隐隐约约地出现,手臂和躯体上的肌肤的确还不错,白中透着弹性,但裸露的手臂已经有了几处色斑。眼神不再单纯,除了知性和自信,还收留了我的风雨足迹,掩映着一些世事后的沧桑与淡定。突然间想起,看手机、写东西、敲文字时,眼前出现的模糊感已经有一段时日,该是需要配备一副老花镜的时候了。曾经自信满满的血肉躯体被岁月烟火磨砺出了现在这副模样,在一声叹息后,不得不面对事实。也许,一个人的衰老不是轰然一声的,是不由自主的,点点滴滴的又悄无声息的在时时刻刻地变化,连贯得只有在小女孩的童真中感觉到,提醒自己应该勇敢地与现实对话。
生命力随自然万物运行。冬去春来,四季更迭,万物从葳蕤生长到枯萎凋谢,再从枯萎中重生,它们没有游走的灵魂,没有缜密的心思,不畏惧枯萎,也不会惦记来年会如何生长,更不必在意应与谁言,是否有人懂,只要一种信念:只要根在,春天一到就一定会生长。在大自然的铁律面前,与万物生长相比,我们不得不低头承认人的渺小。我们从一声啼哭中生,经过繁荣,走向宁静,又从一阵啼哭中离开,不管是辉煌、还是平凡地走过人间,都不必感叹何以有那样的过去和这样的现在,更不必回头和较真,因为都不会重来。
然而,五十岁的年纪也有着独特的魅力,犹如行走在人生的秋季里,收获满满。譬如房贷基本还清,譬如孩子参加工作并谈上了恋爱,譬如父母尚健在,回家还可以真真切切地喊一声娘亲。虽然时光的车轮不会为任何人停下,容颜也日渐衰老,但是五十岁的年纪正在与秋同行,我们应该皈依内心与顺从灵魂,梳理皱纹和白发,把自己还给自己,不必想太多,认真工作,好好生活,在岁月中沉淀,在时光里优雅地老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