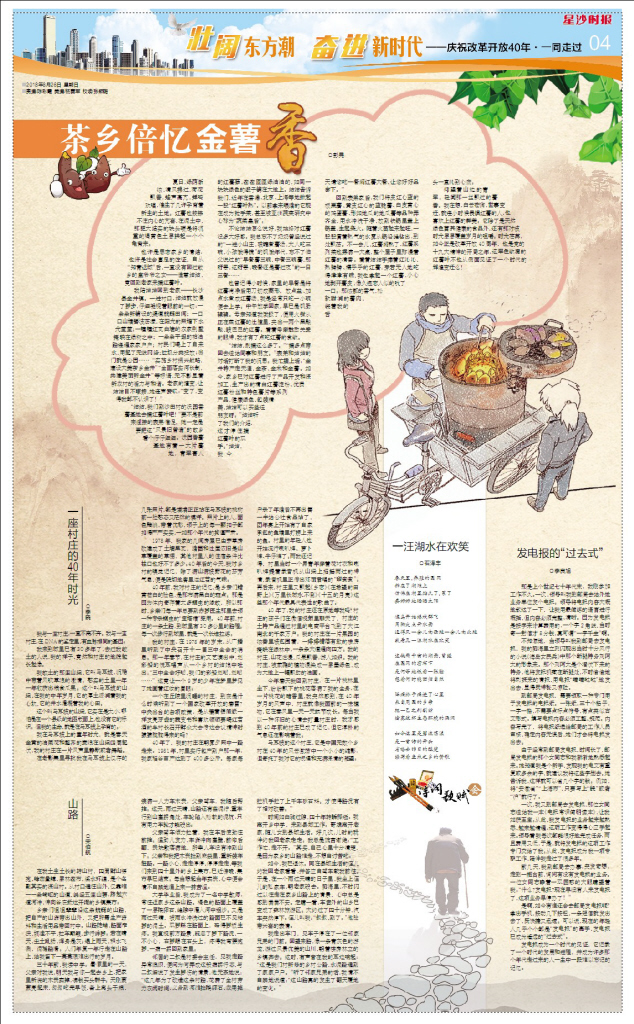◎彭晃
夏日,绿荫渐浓,清风拂过,荷花飘香,蛙声高亢,蝉鸣欢唱,催生了几许孕育着新生的土地。红薯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,在泥土中,那肥大结实的块头硬是将沉重的褐黄色土层拱起一个个龟背来。
也许是思恋家乡的情结,也许是社会富足的佐证,自从“知青返城”后,一直没有回过故乡的堂爷爷之女——佳慧姑姑,竟回到老家来摘红薯叶。
我陪姑姑回到老家——长沙县金井镇。一进村口,姑姑就放慢了脚步,仔细凝视着眼前的一切:一条条新铺设的渠道蜿蜒田间;一口口山塘碧波荡漾,在阳光的照耀下水光莹莹;一幢幢红瓦白墙的农家别墅掩映在绿树之中;一条条平坦的柏油路连通家家户户;村民们喝上了自来水,用起了无线网络;垃圾分类投放;出门就是公园……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建设大美茶乡金井”“全面落实河长制,共建美丽新金井”等标语,无不彰显着新农村的活力与和谐。老家的嬗变,让姑姑目不暇接,她连声赞叹:“变了,变得我都不认识了!”
“姑姑,我们到沙田村的沃园香薯基地去摘红薯叶吧!”要不是前来迎接的表弟催促,她一定是要把这“风景旧曾谙”的故乡看个仔仔细细。沃园香薯基地有着一大片薯地,青翠喜人的红薯藤,密密匝匝绿油油的,如同一块块绿色的缎子铺在大地上。姑姑告诉我们,近年在香港、北京、上海等地掀起一股“红薯叶热”。以前拿来喂猪的它现在成为抢手菜,甚至被亚洲蔬菜研究中心称为“蔬菜皇后”。
不论姑姑怎么说好,我始终对红薯没多大好感。我总忘不了奶奶曾经说过的“一进小山庄,破罐煮薯汤,大人吃三碗,小孩饿得慌”的饥饿年代,忘不了伯父说过的“早餐薯三碗,中餐三碗薯,那呀罢,这呀罢,晚餐还是薯过夜”的一日三餐……
也曾记得小时候,家里的早餐是将红薯淘净后用刀切成菱形,放点盐、加点水煮成红薯汤,我是经常只吃一小碗便去上学。中午放学回家,早已是饥肠辘辘。母亲知道我饿极了,便用火钳从正在蒸红薯的灶膛里,夹出一两个黑黢黢、皱巴巴的红薯。看着母亲鼓励关爱的眼神,我才有了点吃红薯的食欲。
“姑姑,别摘这么多了。”“摘多点带回去送给同事和朋友。”表弟和姑姑的对话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忙插上话:“金井特产走天涯,金茶、金米和金薯。如今,家乡已对红薯进行了产品开发和深加工,生产出的精白红薯淀粉、优质红薯粉丝和特色薯片等系列产品,健康绿色,包装精美,姑姑可以买些送朋友呀。”姑姑听了我们的介绍,这才停住摘红薯叶的双手。“姑姑,我今天请您吃一餐焖红薯大餐,让您好好品尝下。”
回到表弟家后,我们将皮红心蓝的板栗薯、黄皮红心的蓝脆薯、白皮黄心的鸡蛋薯、形如地瓜的地瓜薯等品种弄齐全,用水冲洗干净,放到铁锅里盖上锅盖,生起柴火。随着火苗越来越旺,一股股冒着热气的水雾从锅沿缝钻出,到处飘荡。不一会儿,红薯焖熟了,红薯系列菜也摆满一大桌,整个屋子里弥漫着红薯的清香。看着姑姑手捧着红沁沁、热腾腾、糯乎乎的红薯,旁若无人地吃得津津有味,我也拿起一个红薯,小心地剥开薯皮,像久违恋人似的吮了一口。那浓郁的香气,松软甜润的薯肉,绕着我的舌头一直沁到心底。
仰望着山边的青翠,轻闻那一丝飘过的薯香。我在想,白云苍狗,世事变迁,就连小时候畏惧红薯的人,也喜欢上红薯的鲜美。它除了是天然绿色营养健康的食品外,还有那对被时光层层覆盖岁月的咀嚼。时光荏苒,如今正是改革开放40周年,也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这翠色欲滴的红薯叶不也从侧面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变迁么!
版权所有,未经授权禁止转载、摘编、复制或建立镜像。如有违反,追究法律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