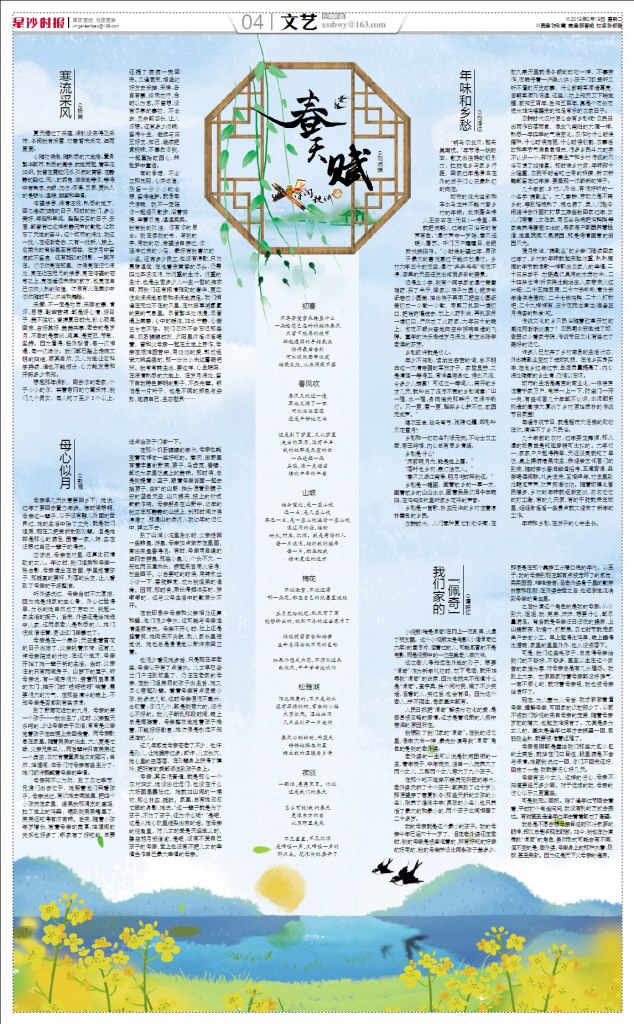◎彭湘
母亲早几天执意要回乡下,她说,过年了要回去置办年货。有时候想啊,母亲这一辈子,似乎没有融入外面的世界过,她的生活中除了丈夫,就是我们姐弟,现在又把爱折射到孙辈。但是她却是那么的满足,围着一家人转,实在没想过自己一辈子的得失。
应该说,母亲在村里,还算比较精致的女人。年幼时,我们姐弟和母亲一张合影,母亲端坐在后面,手里抱着孩子,那挺直的腰杆、利落的头发,让人看到了母亲的干练整洁。
听外婆说过,母亲当时不太愿嫁,因为她是娘家的主心骨,外公过世得早,为长的她自然成了劳动力,挑起一家生活的担子。后来,外婆还是给她选中人家,这两家老人是熟悉的人,她们彼此信任着,便让这门亲事成了。
母亲是在一个寒冬,天空撒着雪花的日子出嫁了,父亲挑着木椅,还有几样母亲陪嫁的什物,在这个地方,母亲开始了她一辈子新的生活。当时,父亲住的只有两间房子,山脚下的屋子,听母亲说,有一间房很大,装着两扇厚厚的木门,推开门时“吱呀吱呀”响着,需要很大的力气,在那些清冷的晚上,不知母亲是否感到有些惊悚。
到了野菊花绽放的九月,母亲的第一个孩子——我出生了。这时,父亲整天乐呵的,少让母亲去干农活,常常是父亲抱着孩子在田埂上来回走着,而母亲歇息在家里。随着弟弟的出生,大人更是忙碌,父亲兄弟三人,而后辈中只有弟弟这一个男孩,农村有着重男轻女的陋习。自然,妯娌间,伯母们对母亲有些生分了,她们或许觊觎着母亲的幸福。
母亲却不以为然,到了农忙季节,兄嫂们出去忙乎,她帮着他们照看孩子。母亲说过,有次她去菜地里,把四个小孩关在家里,结果我那调皮的堂姐,捡了地上的鸡粪,喂到我弟弟嘴里了,弟弟还吃得有滋有味。后来,随着小孩年岁增长,有着母亲的宽厚,妯娌间的关系也好多了,哪家有了好吃的,总要送点给孩子们尝一下。
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,母亲也能变着花样做一些好吃的。春天,田野里有着丰富的野菜、蕨子、马齿苋、香椿,都成为家里饭桌上的美味。那时候,总是我提着小篮子,跟着母亲后面一起去掐蕨子,空旷的山野,抬头便看到镜子般的蓝色天空,山风拂来,坡上的树枝簌簌作响。母亲躬身在山野中,幼年的我立在那静静的山坡上,刹那时间仿佛停滞了,那漫山的绿沉入我幼年的记忆中,挥之不去。
到了山涧小流里涨水时,父亲捉回一些鲫鱼、游鱼,母亲加点紫苏在里面,煮出来鱼香得很。有时,母亲用自编的细网去捞鱼,那些小鱼儿,个头不大,一般也两三厘米长,捞起来后用火焙烤,放盐晒干。以后要吃的时候,用辣椒丝小炒一下,香脆鲜嫩,成为我姐弟的佳肴。因而,那时候,弟长得挺壮实的、胖嘟嘟的,这与父母生活中的勤劳分不开。
在我印象中母亲和父亲相处还算和睦,他们很少争执,这可能与母亲性情温顺有关。母亲不开心时,脸上还是挂着笑,她向来不尖锐,别人家长里短地说,她也总是慢慢地以默许来回应着。
也很少看见她多话,只是现在年老些,母亲似乎有了点偏执。儿女早已各立门户住到城里了,仍住在老家的母亲,在我们姐弟俩的孩子出生后,她又尽心带起孙辈。看着母亲有点溺爱小孩,我多说几句,这时母亲便很不高兴,念叨着:你们几个,都是我带大的,没什么不好的。我儿子断乳那段时间,晚上总是闹腾着,母亲整夜地抱着孩子走着,不能好好歇息,她仿佛是永远不知疲倦的人。
这几年感觉母亲苍老了不少,也许是孙儿,让她操劳过多。或许,儿女长大,她心里的空落落,在孙辈身上获得了填补,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孩子身上。
母亲,其实很普通,就是那么一个农村妇女,她没出过远门,也没在什么大场面里露脸过,她就如山间的一棵树,那么朴实,挺拔。家里,总有她匆匆忙碌的身影,她说:“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,不为了孩子,还为什么呢?”是吧,这是从她心坎里迸裂出来的话。在母亲的视角里,对儿女的爱是天经地义的,碧空朗月般澄澈,是吧,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,世上也没有不把儿女的幸福当作自己最大幸福的母亲。
版权所有,未经授权禁止转载、摘编、复制或建立镜像。如有违反,追究法律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