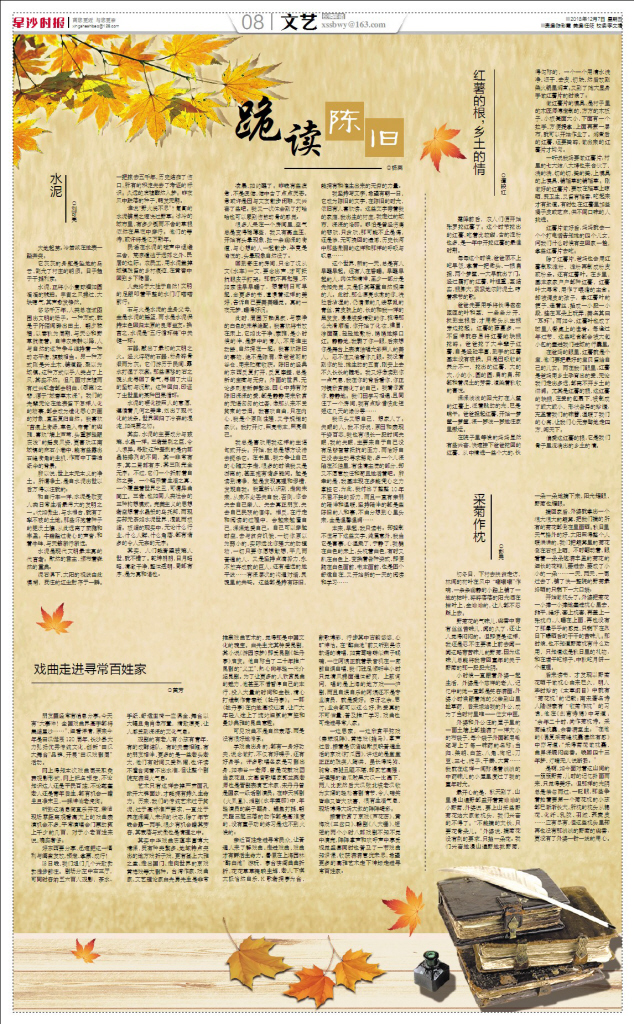◎刘可亮
大地起茧。冷岩浆在地表一路奔突。
它灰灰的身躯是坠地的乌云,刮光了村庄的胡须。日子趋于干挺利索。
水泥,正将小小寰球锢如圆溜溜的琥珀。宇宙之风拂过,大块噫气,其声愈发铮然。
悠悠千万年,人类总在试图围出文明的场子。一种方式,就是于阡陌间辟出田土,朝夕稼穑,以春秋为周期,与天公和野草抗衡着。自神农耒耕以降,人与自然的这种争斗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,旗鼓相当。另一种方式则是兴土木、铺道路,聚以为城镇。这种方式似乎人类占了上风,其实不然。但凡面对废墟而有过兴叹者都会明白,《黍离》之悲,源于“城春草木深”。我们的先辈无论在地表留下怎样人化的物事,都会成为造化悉心刻画的对象,直至复归自然。我喜欢“苔痕上街绿,草色入帘青”的幽雅,喜欢“墙上芦苇,头重脚轻跟底浅”的摇曳风姿,更喜欢江南城镇的麻石小巷中,能有些露出石缝街角的生机,作雨中丁香油纸伞的背景。
所以说,世上本无本义的净土。所谓净土,是自水泥出世以后方得以注就的。
和自行车一样,水泥是改变人类日常生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状如微尘,与水相合,就有了犁不破的土地。那些怀抱着种子的肥沃土壤,从此远离了葳蕤和丰盈。牛蹄踏过街心的声音,和着牛哞,与天籁渐行渐远。
水泥是现代文明最本真的代言者。默然的君主,颁布着森然的重典。
泥石俱下,太阳的视线由此模糊,既往的红尘封存于一瞬。一把抹去五千年,历史结痂了伤口,所有的积淀失去了考证的标识。久远的废墟酣然入梦。昨夜风中跌落的种子,萌发无期。
谁说“野火烧不尽”?匍匐的水泥铺展之速快过野草。冰冷的城市里,有多少锲而不舍的草根依然在黑夜中穿行。他们的等待,或许将是亿万斯年。
民谣在水泥的噬声中退避三舍,荒凉遁逃于远郊之外、民居的边际。农民工,用水泥盖掉城镇残留的乡村痕迹,在黄昏中回到乡下隐居。
人类终于大胜于自然!文明的足跟叩着平整的水门汀嗒嗒前行。
石与火是水泥的生身父母,金是水泥的摇篮,而水是水泥保持本色回归本原的良师益友。换言之,水泥是“五行循环链”中关键一环。
石器,敲出了最初的文明之火。经火淬砺的石器,粉身碎骨煅而为灰。它们游历于民间,露水打湿了衣裳。那些漂移的石之魂从此寻回了骨气,寻回了大山的坚韧与沉默。这种回归,印证了尘世里的某种因果循环。
水泥的硬化按照人的意愿,遵循着几何之美律,划出了现代化的线条。世界回归了冷森的混沌,如鸿蒙之初。
其实,水泥的主要成分与玻璃、水晶一样。三者差别之巨,令人惊异。导致这种差别的是内部晶格排列的不同,其一非常有序,其二局部有序,其三则完全无序。不过,它们一个折射着自然之美,一个昭示着生活之真,一个覆盖着世界之丑,可谓异曲同工。三者,也如同人类社会的三种构想模式。完美主义的思想者空想着水晶般的乌托邦,而现实却无奈如水泥世界,混乱而板结。板结的现实中,无论什么行业、什么人群、什么角落,都有诸多的令人无奈的无序。
其实,人们能奢望玻璃人世,就不错了。乾坤朗朗,日月昭昭,清澈干净,整体透明,局部有序,是为真和谐也。
版权所有,未经授权禁止转载、摘编、复制或建立镜像。如有违反,追究法律责任。